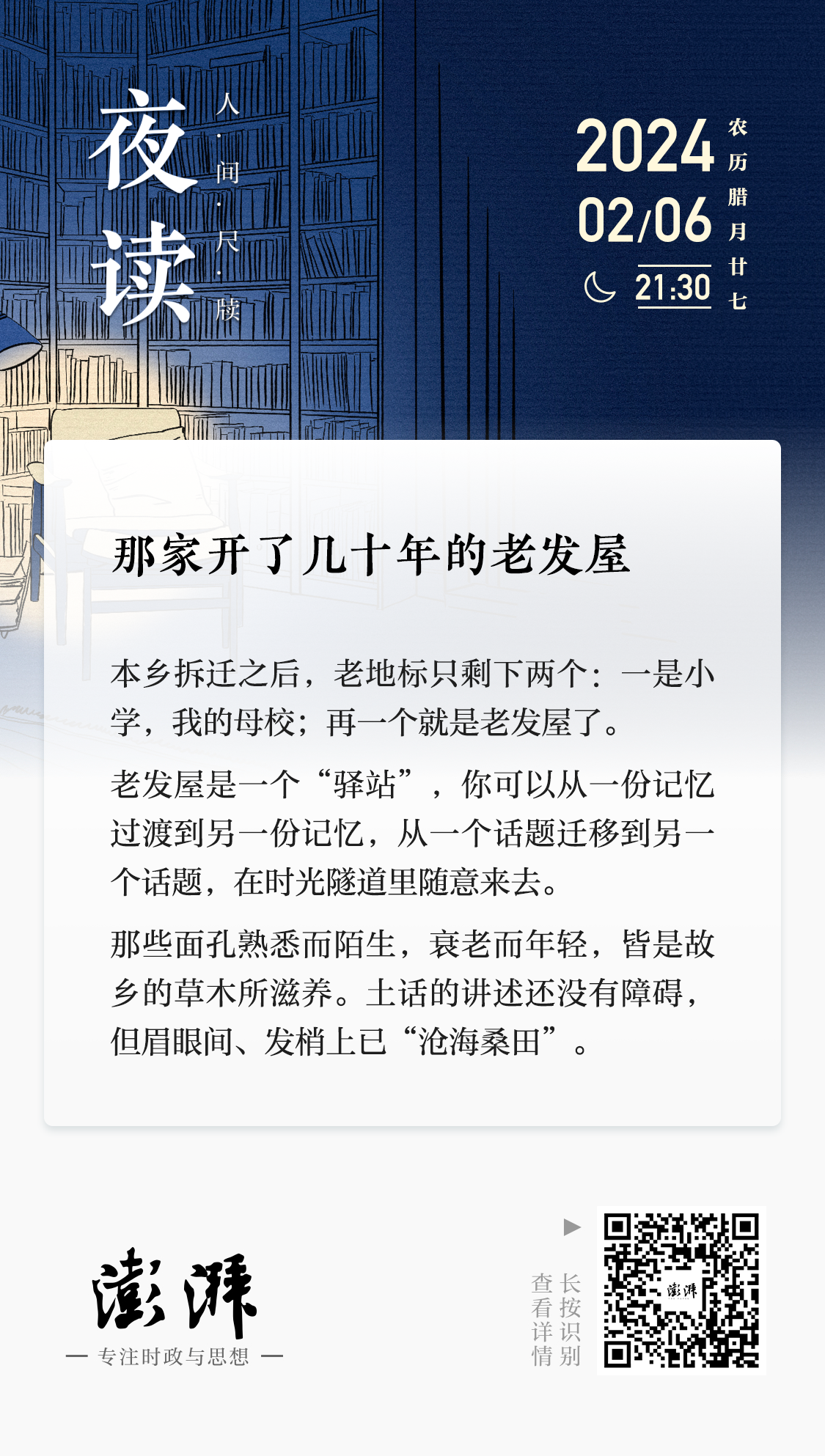我的老家在南京江宁。十年前,本乡拆迁之后,乡中心地带只有一条大马路保留了下来。这条大马路,连着青龙山和旧日县城。马路两边原是各式建筑,高矮胖瘦皆有。人烟密集,尘埃不落。
如今,只有局部的建筑还在。可以继续成为本地人一眼“会意”的显著地标有二,一是小学,我的母校;再一个就是老发屋了。老发屋店主打的是地名烙印,相当于告诉你,理发师来自江宁的丹阳。
有一次,去乡下看父母,父亲饭后说要去“小丹阳”理发。我吃惊,小丹阳可是在几十公里外,去那么远干嘛。他说,“哪儿啊,就在我们的上坊街上”。于是才知道,“小丹阳”是一间发屋的简称。来自“小丹阳”的理发师和两个儿子在上坊老街开店几十年了,父亲一直在这家店里理发。父亲一再强调,他们理发理得房子都买上了。
我不知道我小时有没有感受过他们的手艺,但是瞬间来了兴趣,表示要和父亲一起去“小丹阳”理发。
这些年,我理发像流浪,“理”无定所,谁家理出的发型不犯嫌就可以。但老实说,除了一对中老年夫妻开的“青春理发屋”外,我没有特别满意的去处。自从经营多年的“青春理发屋”在我的住所附近莫名消失后,我的选择面更窄了。那些新潮的发屋,再也没有传统留梯形鬓角的习惯,而是直挺挺地推平鬓角,让我难以接受。每次理发,都要反复和理发师解释,如何理出合适的鬓角样式。但说了白说,只能逐步妥协。
父亲带我去的这家老发屋,像是可以专治我的烦恼。理发师扫了一眼我的头型,无须我多言,咔咔就下剪。传统工艺,主打一个“流线型”效果,关键是便宜:理发12元,理发加刮胡15元。硬要挑毛病的话,那就是“费时间”——理发师如同承包了一项工程,认认真真地打理,不带一点敷衍。
从此就形成了习惯:每月到此一剪。
下次再来时,他都寒暄一句:“到你父母家吃饭的啊?”理发师第一次就记住了我。老理发师早已不剪头,只给顾客刮胡子。那刀刃铮亮,刮前照例在皮子上蹭几下,算是加一点锋利感。也不多蹭,蹭多了那叫“出新”了。
年少时,上坊老街有个外号叫“二轮子”的老头,喜欢挑着剃头担子到处吆喝剃头。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自己的理发店。想来是有的。
我上初中时,不知道是哪个调皮鬼把我喊成“二轮子”,迅即传开,简直莫名其妙。我既不戴眼镜,也不骑“二轮”,长相也错老远,哪儿也挨不上“二轮子”。直到我离开本乡上县城读书,才算成功“洗名”。
“二轮子”的理发功夫真不赖,我喜欢他掏出刮刀蹭皮子的嚓嚓声。实事求是地说,这种声音难以精准形容,非常带感。
“小丹阳”老发屋里有四把工作椅,是铁制的,斑驳不堪,但不锈。屋子里地方不大,经常挤满了老客。人来得再多,理发师也不急,就一句:“先坐下啊。”然后就投入“头部”事业中,任你等。过程中极为专注,极少和顾客闲聊。也不用叫号,该谁刮,该谁剪,全凭理发师朝你点点头,像是对暗号。
“排位”在他们的脑子里,丝毫不错。这边甲洗头,那边还能凑个空当给乙修两剪。他们是时间控制大师。等待的过程中,可以和故乡各样的久违者打照面。
后来发现,老发屋还可以代存、寄快递包裹,牌子上写了,存件的话,每件收五毛钱,取件人不用出这个钱。想想,老发屋还真的是一个“驿站”,你可以从一份记忆过渡到另一份记忆,从一个话题迁移到另一个话题,在时光隧道里随意来去。这边放着抖音,那边回到1980年代,也不违和。
有些“面孔”来自30多年前或者更早。那些面孔,熟悉而陌生,衰老而年轻,皆是故乡的草木所滋养。土话的讲述还没有障碍,但眉眼间、发梢上已“沧海桑田”。和他们聊上片刻,沉默半晌。我和他们曾经共同经历的事件,多数再也想不起来了,只好一遍遍地被记忆弄伤了。